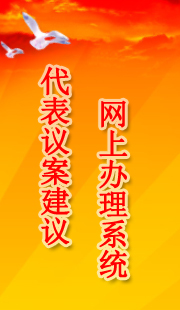作的剧本《精忠旗》,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。岳飞遭构陷后,负责案件的大理寺丞李若朴的同行何铸,是一个小人物,虽不免软弱、自私,但又是良心未泯的人,“公心拒谳”中一段唱道:“唉!这样一个忠臣,何忍将他陷害?也罢,如今世上的人,不知做了许多没天理的事,也不见报应,难道偏我何铸一弄就弄出来不成?”在何铸看来,天理显然是公平、正当乃至是良心的代名词,精忠报国的岳飞受到非公正的构陷,被与天下人的“没天理”等量齐观了。
不止是在戏剧中,在现实生活中,“没天理”、“天理何在”、“天理良心”等也成为很多中国人遭受冤抑、不公的共同表达。一句“没天理”,反映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失望、无奈,同时又隐约包含着对实现公正的某些期待。事实上,天理不仅是一个日常用语,它更构成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,“天理国法人情”不仅被镌刻在负责审判的衙门之上,更是历代清正严明的司法官员共同的追求。虚无缥缈的天与人间俗世的“理”何以连接起来,天理又如何与人们的公正、法治观相联系,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内在脉络中寻求答案。
中国文化中“天理观”的历史演进
自先秦以来,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,主要是世俗化的,更关心社会人事,正如季路问事鬼神,孔子回答说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治乱既非天命,则天人不相干涉。汉代以降,儒家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,董仲舒提出了“人副天数”的想法:“天德施,地德化,人德义。天气上,地气上,人气在其间。春生夏长,百物以兴;秋杀冬收,百物以藏。故莫精于气,莫富于地,莫神于天。”此时,具有本源性的天与世俗人间的关系开始建立,“天地之符,阴阳之副,常设于身。身犹天也,数与之相参,故命与之相连也。”在董仲舒看来,水旱、地震等自然灾害,并不完全是出于自然规律,而是缘于人事,自然的异变实际是对皇帝执政不当的谴责,所以当灾害或异变出现时,皇帝必须修德改政,若对此忽视不惮,则王朝就会灭亡。
唐代以后,对源自于天的自然灾害又有了新的认识,很多人认为灾害不过是“常数”、“常理”,它是自然的机制产生的自然现象,与人事特别是与皇帝的德行无关,此种认识一直延续至北宋,由此还出现了“天是天、人是人”的天人二分的思想,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。尽管天人关系得以分离,但并未完全分裂,特别是有关皇帝对于天命负有道德责任的看法,仍承继了天人相辅的观点。北宋思想家王安石认为:“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,天地万物不得其常,则恐惧修省,固亦其宜也。今或以为天有是变,必由我有罪以致之,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,何豫于我?我知修人事而已。”他反对两种极端的看法,认为其不免愚昧、“固怠”,对待天之异变正确的态度是:“以天变为己惧,不曰天之有某变,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,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。”也就是说,不必在天变与人事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,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,认为天之变异与人事完全没有关系,而应保持有对天的敬畏,特别是需要以“天下之正理”来检讨人事的过失。
宋代理学发展,以朱熹、程颢等为代表的理学家,又将儒家的三纲五常抽象为天理。朱熹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天理的表现,“天理民彝之大节”,“其张之为三纲,其纪之为五常,盖皆此理之流行,无所往而不在。”因此,“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,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件数。”既然亲亲尊尊的纲常是天理,如果有所违犯,就是悖逆天理,要受到不可饶恕的处罚,其目的主要是维护君权之至高无上,以及等级、伦理秩序。面对南宋的社会现实,朱熹继续发展了天理人欲之说,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,认为二者不能并存,必须存天理、灭人欲,只有在“革尽人欲”之后,才能“复尽天理”。程颢则认为,“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”,“万事皆出于理”,“有理则有气”。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,遵循它便合天理,否则是逆天理。朱熹等理学家的学说尽管不无偏颇,但它将虚无的天理与真实社会的伦理纲常联系起来,使得天理在世俗中的规范性更加明晰。
中国法文化中“天理观”的法律内涵
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,早期并未出现明确的天理概念,但与之相关的“天”、“天命”等则早已有之。西周初建,周人对商人的天道观进行调整,否定了上帝即祖宗神的观点,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,并使之为君,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。战国时的管子,提出“生法者君也”,但君虽生法,并不是凭自己一己之私心,任意为之,而必须以天则人性为标准,“天则”即是自然界不可违背的规律,表现与俗世,则是人之者为人类本能中之好恶,源自“天则”的人情好恶即是立法之重要标准。
宋明以来,天理渐渐成为司法审判的重要渊源。在南宋的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,真德秀阐释了他对天理、国法的理解:“是非之不可易者,天理也,轻重之不可逾者,国法也。以是为非,以非为是,则逆乎天理矣!”在真德秀看来,天理即是审判中客观的是非,不分是非就是悖逆天理。在清代,司法审判中各种天理的用例更为多见。乾隆八年,“刘元熙、刘元照商同谋杀胞弟刘满仔起恤,以致伊父刘奇英、母李氏俱被刘方通、李世顺立时杀死。乃刘元熙等忍心灭性,既不首告伸冤于前,复敢抬尸弃埋于后。”刑部奉旨驳回,判语中说:“其逆恶之罪,已为天理人情所不容,又岂国法王章可少贷。”嘉庆年间,大名府知府张五纬,遇到一件儿子遭人殴打并无意中向其父亲说起这件事,愤怒的父亲与其一同前往报仇,结果父亲遭受伤害的案件,张责备作为肇事者的儿子:“揆诸天理、人情、国法,实属罪无可逭。”这些案件中的天理,即与人情相通的“天之正理”,都用以形容犯罪的性质极其恶劣,到了天人共愤的程度,故国法中绝无通融宽赦的余地。
有的案件中,天理又被作为人情国法难以调和时对二者加以折衷的办法。道光末年,江西发生一件婚姻案,订有婚约的两个家庭之间,因为发生斗殴而引发诉讼。尽管斗殴事件已经被解决,但女方一家却因此怀恨在心,试图解除婚姻,而男方不同意,双方遂起官司。负责审理此案的鄱阳县的沈衍庆也颇感为难,“盖闻父子夫妇,并重于大伦。国法人情,必衷诸天理”,从国法的角度,仅仅由于之前的斗殴而解除婚姻是不能承认的,但从人情的要求看,又不应强迫不情愿的女子嫁给对方,因此需要诉诸天理对二者予以调和。沈衍庆最终的判决是,该女终生在父家中守节,男方则不得娶妻,但可纳妾,他认为“如此一变通间,庶伦纪足以相维,而情法似觉兼尽”。这一案件的具体判决,尽管不无商榷之处,但通过天理折衷人情国法的方式,无疑体现出天理的本源性、重要性。
概言之,在中国法文化中,天理即“天之正理”,它是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支配法则,是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,高于一切人类社会法律的权威,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公平、正义的终极理解。天理高于国法、人情,从而可以对发生冲突的二者进行指引。
中国法文化中“天理观”的现代诠释
自科学主义兴起以来,一切未经科学的、实验的方法验证的知识,均遭到批驳,天理的观念自然也是如此。然而,回到生活的实际,在中国社会,我们又不时地听到、看到各种各样有关天理的表达,这也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“天理观”的现代价值。
中国自清末西学东渐、变法图强以来,吸收、建立的基本是以西方法律为中心的现代法律体系,善于学习他人之长,本来无可厚非,但在此过程中若彻底丢失了中国自身的特色,失去了中国法治话语权,以及中华法律文化自信,也不应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法治图景。要重新掌握法治的话语权,实现法治的中国化,就需要挖掘具有合理性、适合现代中国的传统法治资源,去除虚无、伦常等不合理因素的“天理观”,正是传统法文化中值得重视的理论资源。
深入解读“天理观”,有助于理解老百姓的公正话语。现代法律知识尽管极为发达,法律教育日趋普遍,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,仍然局限于他们所理解的法治、公正之中,并使用他们的话语来描述。当“天理何在”这样的表达出现,已经反映出他们对无法提供正义的当代法治的极度不满、愤懑,司法的公信已经隐隐地显现出危机,如果再不加以重视,很可能面临着法治的“溃败”。
传统法文化的“天理观”,也启示司法者需保持敬畏之心。何为天理,它就是人世礼法的超验性依据,就是我们不能用利益、科学等经验去检验它,它是我们信仰的对象。换句话说,天理就是法律所依据的根本道理。作为司法者,在利益衡量、科学检验之外,还需要对冥冥中的公平、正义保持敬畏,以认同天理的“良心”来审断案件,对待民众,最终,经由司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