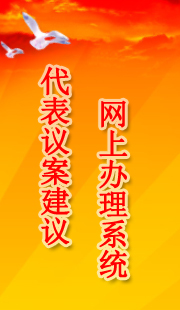鸡鸣唱晓
崔学锋
晚饭过后,刮了一天的大风渐渐止住了。
躺在床上,他辗转反侧,听着屋外虽已渐刮渐小但仍余势未绝的风声,他躺不住了,干脆掀开被子坐了起来。
“又抽哪根筋呢?”一旁的老伴其实也一直没睡着,只不过他心绪太乱了,没有注意到而已。
他没吱声儿,从枕头底下摸过烟盒,抽出一支,打火点燃,一口一口深深地吸起来,烟头暗红的火光一闪一闪,勾勒出他心事重重、被腾腾烟雾包围着的暗黑色轮廓。
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人代会了。
他已经是第二次当选县人大代表了。
想起第一次当选时,临行去县里开会前,他也是几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不过,那个时候,更多的是……是什么?好象有喜悦、兴奋、激动、期待,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莫名其妙的忐忑、紧张,如同一个稚嫩的学童第一次走进肃穆神圣的考场,不知道自己的答卷是否合格,能否入了考官大人的慧眼;又如同一个毛头小伙儿第一次穿上别扭的新衣,由媒人领着去姑娘家里相亲,心里既甜丝丝、美滋滋的,又实在是七上八下如鹿撞一般,想着那对方是个什么模样儿,又能否看得上自己……
初春的夜月爬上来,透过窗棂照在炕上地下,光影被框成一格一格的,模糊而惨淡、杂乱而凄迷。
他微微叹了一口气,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人代会了。
按说,有了第一次的经历,第二次应该是从容、沉着、胸有成竹,可他就是静不下来稳不下来,心里象长了一丛讨厌的荒草,又像着了一把火。不知道是临战前的亢奋,还是心无底数的惶惑,抑或是对此行渺茫的担忧——似乎什么都有,心里满满的,连喘气都不那么顺畅;又似乎什么都没有,空空荡荡得直叫人没抓没拿。反正,反正他就是睡不着。
他又摸出一支烟,顿了顿,却没点上。屋外夜风轻呼,窗纸低语,似有柔弱纤细的新虫声儿若断若续地随风传来。他抓起烟和火,翻身穿鞋下了地。
走出屋外,尽管凛冽的夜气使他连打了几个寒战,他还是为这大风过后的天高地阔由衷地感到开怀。天上斜月朦胧,河汉微明,北斗阑干,柄把东指,又一春了哇!
他在院子东头的矮墙边坐下来,又不由自主地摸出烟和火,抽着,沉入对往事的回想之中。
人代会闭幕后,他所提的关于本村乱砍滥伐、毁田挖沙的提案由镇政府负责落实。可当他满怀信心地赶到镇政府时,接待他的那个一脸浮肿的镇长却让他坐了一上午的冷板凳。将近中午,把他晾晒得差不多了,那镇长才忽然想起来他似地问道:“你有什么事吗?”
他的话里不免带有几分火气:“镇政府是人代会提案的承办单位,请问我们村乱砍滥伐、毁田挖沙的事情怎么解决?”
镇长眯缝起那双肿泡烟,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,才说: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那事儿你能管得了还是我能管得了?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,你的老脑筋要改改啦!”
“狗官!”他在心里骂道,深知从这号人嘴里吐不出人话来,他起身摔门而去……
一支烟完了,他又接上一支,一支接一支。舌头嘴唇全麻了,抽不出来烟是什么味道。
后半夜了,不知从谁家的鸡窝里,传来几声睡意迷蒙、粘涩无力的鸡啼。
这平日里听惯不怪的鸡啼声,此时却简直如醍醐灌顶、仙乐绕耳一般,他脑海中灵光乍现而遽然惊觉:被人蔑称为扁毛畜牲的公鸡尚念念不忘司晨之职,何况人呢?在其位谋其事,既然大伙选了你,你就得替他们说话,代而不表,算什么玩意儿?还不如一只不会说话的畜牲吗?人代会上有咱农民的一席说话之地,事关农民兄弟们最关心的事儿,这届会议上我还要说!大说特说!说了就有希望!
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公鸡加入这黎明前的第一次大合唱,声音也越来越利爽、清脆、嘹亮起来。
他又想:说了以后还落实不了怎么办?那就不厌其烦地去找承办单位和责任部门,一遍两遍不行,那就三番五次十来八次去找!鸡鸣也不是一遍两遍就可唤出红日东升的嘛……
他果断地在地下拧灭最后一枚烟蒂,站起身来。
浩瀚的长空中风露苍茫一派,正涌动着无涯无际不可阻挡的滚滚春潮;
一颗硕大、灿亮、沉静、不群的启明星正气度雍容地镶在西天;
天与地的交界处,正孕育升腾着庄严盛大的黎明;
所有的希望,都如万千含苞的花骨朵,一齐绽放在这乳汁般甘美的黎明之中!